□杨健民

翁琳琳/摄

翁琳琳/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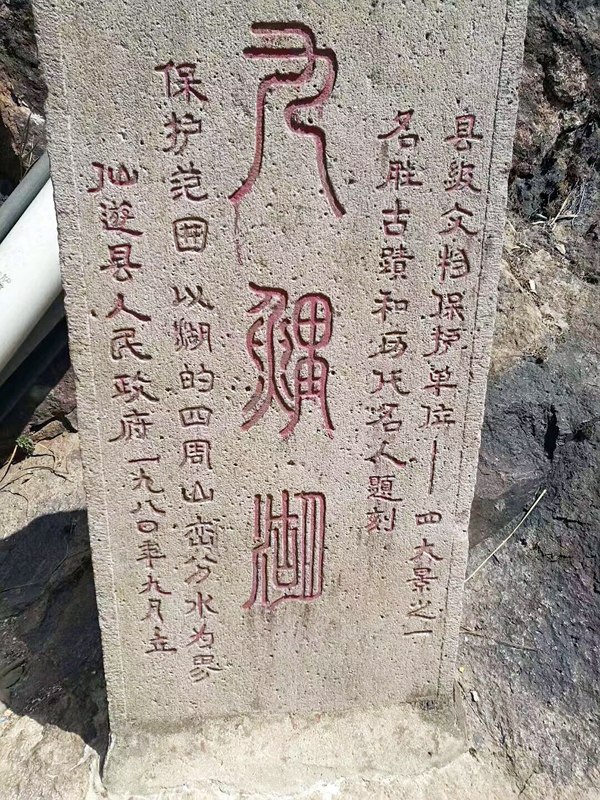
翁琳琳/摄

翁琳琳/摄

翁琳琳/摄
仙游,一直被人们从地名上去想象,是一个神仙来过的地方。1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一大批自然之美和人文之胜。打开仙游地图,突然发现那就像一个人头,无论是男还是女,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安静的心跳。
我生在仙游,在那里生活了22年。这个县域自西北而东南逶迤延伸,整个头部派山,后脖颈直接吻海。没有落叶的季节,从龙眼树、文旦柚到枇杷,所有的植物都在亚热带的温润气候中枝繁叶茂,绿意葱茏。历史擦肩而过了多少年,即便有一些灼目燃烧的片断,风流云散,阳光下的日子依旧灿烂。在县城小巷抑或乡下某个幽深的村落,或许会突然嗅到某些往日的气息。可以肯定,仙游是有历史的,它们不断地再度返回,或者拐了个弯再度消失在某一段滚滚红尘背后——这就是仙游的寂寞和热烈,安静和喧闹。但无论如何,我忘不了仙游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即便这里还存留着一些晦暗不明的历史交叉点,我都会记住这里的人间草木,记住那些长河落日般的历史记忆。
同时,我还觉得仙游的山水是率性的,像是酒后的泼墨和行草一般,浪漫无羁。即便是一处危岩,抑或一泻细瀑,都具意态奇崛之像。天工是一管纵横恣意的大毫,一勾划,一顿挫,都成狂放之势、跌宕之势和欲飞之势。有时擎天一柱,犹如孤灯一枚,行书的笔意嘎然而出;有时象形一石,则可任由想象,随心所欲。我甚至想,如果说九鲤湖在研一池墨,麦斜岩在提一管笔,菜溪岩铺陈的也许就是一张纸,满纸奔走的是天马行空的千万年历史积淀。仙游的山山水水原来孕育那么多的故事,如今却是安静地匍匐在我的脑际。竖起耳朵一听,那里藏着许多诱人的热闹。所以说,仙游这个县域有一种优雅的静止。一棵树的重量是静止的,一座山的永恒是静止的,静止就像契诃夫剧本里经常出现的那个舞台提示:停顿。在停顿中有一种穿越人心的东西开始流淌。
似乎是轻轻地吻了一下,在仙游这个头像形态里跃出的山水形胜,以及名居老厝、烟霞古道等,所有的聚拢和敞开,都让人们意识到了“看”或“游”的能力,都使得仙游这些风光在人们期待的眼神中前所未有地丰富和活跃起来,并且开始了一场视觉的远行。
美丽和遐想、自然与人文,都凝固在这一片或由心造境、或由境生心的境界之中,一切皆凭心悟,表现出一片自然、疏野的心性。在我看来,对于仙游山水的诠释,以及对于景象的读解,都可以在一种自然和人文生态诗学中保持娓娓而谈的视觉冲击力。那里,山峰也许是欲飞的,草木也许是尖啸的。所有这些动或不动的景色,诉说的就是千万年的精神撩拨。
仙游这一大片率性无羁的山水名胜,它所展开的不只是视觉与世界的直接撞击,而是在视觉之中隐含着一种思索。“视觉即思索”——这是当代文旅的一种新理念。对于揽胜仙游,我们的视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瞬间定格的浓缩的历史,这就是思索的历史,它们既是传统的,又是平民和原野的,这是视觉思维和文化思维的胜利。我们的确不需要过多的隐喻或机心,只要意识到我们的视觉是在远行,是在积累自然的神话和脚印,这就够了。
比如九鲤湖,那肯定是一个神话的存在。我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去了九鲤湖,对九鲤湖的认识也是很晚的。20世纪80年代,我两度去过九鲤湖。奇怪的是,在这里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感觉。这并不全是因了九鲤湖可以赐梦给你的缘故,况且我还没有向她祈求过什么梦呢。我只是感到,这一汪湖水,甚至那一窝一窝据说是仙人脚印的石臼般凹下去的水坑,都沉浸着某种象征性的文化意义。
有一次是陪着我的恩师许怀中教授前往九鲤湖的。记得当时已是枯水,不见了瀑布,便更觉得这里安静得像梦境。许老师祖上就住在九鲤湖边上,想过去他大概是沾了九鲤湖的不少仙气。他一进入九鲤湖竟然像换了个人似的,持续地兴奋不已。那一刻,我意识到在我们的人格结构中,可能就缺少一种这样近乎调皮的情绪张力,因而常常把我们自己弄得太逼仄,颠簸得过于认真。多一些爽朗和快意有什么不好?无论是纵身一跃,还是登高一呼,都是一种潇洒,都是一种轻松的活法。就像来到九鲤湖,无须去作过多的物化转换,只是凭着你自身的感觉,凭着你情感的流程,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层层涟漪。这就很美。
这就是境界。
人要达到如此的境界是不容易的。人,往往贮积了太多的期望,于是变得没有期望;往往汇聚了太多的想象,于是就失去了想象。匆匆来到九鲤湖,祈梦是来不及了,那就抽支签吧。开始时都挺单纯,心想抽一支便算数。结果,抽了第一支,便想再抽第二支,于是第三支、第四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亵渎。就像那宁静的湖面,本来可以照出你的容颜,你却偏偏又去抚弄了一回,荡起的水波便立即使你变形,留下的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幻影。
我的脑子里立刻闪现出“随缘”二字。随缘之难,就难在“随”字上。随是一种主体意识,是一种极其抽象然而又是极其现实的人格力量,是一种大彻大悟。
于是,我想到西子湖畔曾经站出来的那个林和靖。这位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来咏梅而成为千古绝唱的隐士,仅凭梅花、白鹤和诗句,就把隐士做得那样地道、那样漂亮。这看起来似乎并不难,但作为中国文人的一种自古而然的情趣——自得,我想多少是要下点功夫的。有了这个自得,它就使得我们站在一个也许不算太机智的立场上,让一个小小的顿悟维持了内心的平衡,于是就有了一种自以为体味到了快活、体味到了轻松、体味到了潇洒——当然最终也就体味到了随缘的心满意足。
九鲤湖是一个有故事和历史传说的地方,一个有梦的家乡。梦境的造化,历经了多少代人的传承,如今成为了一种拂逆不去的文化符号,也承载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内容。然而,如同其他历史文化一样,九鲤湖的梦文化也是要远行的。它的每一次远行,几乎都向着它的古老家园和历史记忆的再度返回。所以,仙游县应该对九鲤湖梦文化作出新的宣传和重塑,对九鲤湖梦文化的格局重新确立和重新定位——这才是对于仙游历史文化记忆的复活,才是体现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一种文化良心的觉醒,一种文化记忆的觉醒。对于每一位关注仙游历史和九鲤湖梦文化的人来说,九鲤湖的独特魅力决不是我们这几代人能够消费得了的,它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无可泯灭的梦文化的记忆,我们也将把这种文化记忆留给后人。
历史对我们的设计,有许多并不是留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而是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文化的兴亡,从来都是从唤醒或者毁灭记忆开始的。唤醒一种记忆,也就唤醒了一种文化;而毁灭一种记忆,也就毁灭了一种文化。法国作家雨果在1835年写了《向拆房子者宣战》,当时他看到一座钟楼被拆除,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这是把城市的记忆给毁灭了。法国后来对城市文化、文化建筑为什么会保护得那么好?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前瞻性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所具有的历史眼光,使得他们不仅站在现在看到过去,还站在过去看到现在。仙游的一些有识之士,对于九鲤湖梦文化的憧憬,我想同样是在复活一段有生命和有记忆的历史存在。这种存在无疑是恒久的。
在九鲤湖,我不知不觉地掉进了一个古风蕴藉、文气沛然的深潭,说不清这水的摩挲是不是已经沉浸着一种人与美的奇异的造化,也说不清古人常说的“古池好水”是不是在这里留下了一脉遗音残响。水汽冉冉,梦境依旧,我感到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情怀,仿佛就在这里裸裎。我想唯有在这里,唯有在这个时刻,人的梦境和情思,才会从混沌未凿中抽出,重新凝入心底,并蔚成一种超拔的生命方圆。假如生命也是这样的一座湖泊或者一座梦境,我们该在那里留下一脉怎样的精神气息?
对于仙游,我不禁对这一座头像般的县域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我觉得我是再度遇见了仙游。遇见就是抵达,这不仅仅是属于我自己的抵达。一个人内心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你第一次走出来的那片土地。怀旧是一扇不灭的窗口,从那里望去,最遥远的,也是最亲切的。所以,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的“念故乡”一节,总会让我想起故乡,想起那一去不复返的年少时光。当年,米兰·昆德拉离开家乡布拉格去了巴黎,他付出的痛苦和悲伤便成为他的心灵的祭坛。昆德拉的小说是一部怀旧的诗,为了发现人类存在的隐秘之处,他的内心不断地在流亡。然而往昔已然逝去,重返不再可能。任何被遗忘遮蔽的世界,都将是我们心灵返乡的起点。多年来,我一直对“子在川上曰”这几个字怀有莫名的冲动。人,什么时候有了那种流失感呢?“逝者如斯夫”固然是一句老话,庄子的“忽然而已”也已了然于心,然而,我在心灵里沉入仙游,总是在享受着一种我试图真正抵达的抵达。
我们的视觉正在远行,我们的心灵也正在抵达。仙游的那些行迹语言,正在悬浮起一个新的叙述空间。我确乎无法概括甚至无法准确描述这么一种视觉美学,我只能说,我们需要打开山水知音的某种情趣,并且抵达自然神话和人文历史的某个深部。因为我的感觉已经被那种“看”和“游”的氛围和意象遮蔽了。
于是,我看见了“霜叶红于二月花”,也发现了“云破月来花弄影”,难道谁还会对此视而不见吗?我想,在仙游之内或之外的任何人,只要心性未被泯灭,都可能有不羁的视觉和诗性思维。人生匆匆,我们总是把人生当作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而无暇顾及身边的山山水水和花花草草。凡是对人生沧桑有了一些历练的人,都会意识到我们需要诗意,需要闲适,需要走神,需要将身边那几声间歇的蛙鸣或者鸟儿啁啾细细地默读一遍。这时,人就立刻会万虑俱泯,一心澄然,无所思亦无所忆,人生的弹性、心智的自如以及人的许多了悟,都可能在这里出现。
如同武夷山有刚直的理学和朱熹,也有放浪的风流和柳永,仙游有三朝元老郑纪和杰出的思想家蔡襄,也有名闻遐迩的九鲤湖、麦斜岩和菜溪岩。曾记否?当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不就是一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模样。宋词是怎么唱的:“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位理论家承认:“什么是诗意?诗意就是一种难言的韵味。”那么在我们的视野里,仅仅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么?我们还能不能找到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里说的“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那样澄然的诗意么?
此刻,当我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仙游县域这座头像时,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仙游山水那些动人又动情的故事时,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与仙游遇见时,我已经迅速地从这些历史叙事中抽离出来,悠悠地与清风对话,与明月相望,去做一次视觉的远行和心灵的抵达。由此,我意识到有一种旁观的快乐和一个新的山水和历史的神话正在骤然降临。
2024年3月28日

